陈嘉映|总有人劝我“要现实一点”,而我始终不明白
- 时事
- 2025-04-05 12:52:05
- 4
【编者按】
《旅行人信札》是学者陈嘉映1981年旅行时写给北京亲友的25封书信结集。其时,他就读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临近毕业的春天,他花了两个月时间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以下是其中第24封信,是他写给哥哥嘉曜的,记录了5月15-17日,他从苏州到上海的经历。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嘉曜:
不是独处,难能随时记录。今六时起,不久同小琳出门,到南门坐市郊车往西南到木渎,登灵县风景之一灵岩。一座不足200米的小丘,顶上有座庙,一个公园和一堆堆游人。天阴茫茫的,看不大清太湖,虽然离得很近。庙里的素面好吃,吃了两碗。然后好走了一段路,到天平山。这山上的石头生得还好,毕竟同南普陀无法比。题刻也多,字往往写得不错,意思却难解:一汪脏水(从前可能是清的)说是吴中第一水,三十米高处写着凌云倚天,一片小石板题作天屏、势盖五岳,等等不一。写诗题字固然需要一点想象力,但直弄到颠三倒四,就难怪人们要笑文化人无聊了。
小琳“腿软了”,只登到天平山半。在那里看见苏州人同上海人大打出手,头破血流。上海的年轻游客老嘎嘎子,到处摆出洋气阔气什么都看不上眼的样子,买东西时却精打细算,不惜屈尊和小贩斤斤计较,得便还要欺负乡下人。他们绝不肯在任何事情上吃亏。乘两站车,也拼了命抢位子;无论旅行到哪里,总不忘打听茶叶、饭碗和小椅子的价钱,设法把便宜货买到手,带回去。语言轻薄,无视公德,招惹是非。
而我亲交的上海人给我的印象却大不相同:生得干净漂亮,头脑清楚,精明强干,胜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切方面的工作;工作勤勉,处世谨慎;情愿为享受多出力气,不习惯坐享其成。当然也有点喜欢议论别人,关心自己多一点儿。上海人,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外地,始终在生产着中国第一流的东西,但他们似乎不曾为自己产生相应的威信。
……
两个月来,饱览江山胜迹,见一山爱一山,见一水爱一水,然而,并无一时不惦着北京,北京的文化气氛和政治热情,标准的普通话,北京的阳光(哪怕带点风沙),天坛雪茄(不曾脱销吧),桥牌赛,北京初夏的傍晚。归根到底惦着北京的人,那些我们爱的,爱我们的,我们关心的,关心我们的,那些在哲学方面同我们的追求一致而在风格上同我们互补的人们,那些不计较功名欲利却意气风发的人们,那些从忤逆无常的运气和恒定的命运中同样赢得快乐的人们,那些摆脱世俗标准而仍坚持着标准的人们,那些我们的进取为了他们的骄傲而我们的失望依赖他们来安慰的人们。
从天平山坐车回南门,步行到沧浪亭转了一圈;去拜访陶伯伯,他上中班去了,同陶伯母小叙。用过点心,告辞出来,在怡园转了一圈。叔叔已买定了明天午后的车票,我只好待到明天午后了,干脆多逛逛吧。这江南温柔富贵之乡,享用也享用不尽,写也写不尽。早有柳郎的望海潮,欧阳永叔的采桑子,以及其他无数名篇,吾生也晚,何必浪费笔墨,直抄一阙韦庄可也!
人人都道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画舫听雨眠。
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需断肠。
[卖豆腐脑的姑娘也个个西施似的]
晚饭闲聊后偕小琳到食品厂拜望陶伯伯,又说是白班,回家去了。
叔叔对我赞誉有加,同时劝我要善用自己的才分,不要太脱离了实际。从小起就不断听人劝我“要现实一点”,而我始终不明白我怎么不现实了。难道一定要把一切想象都打扫干净才有一个现实剩下来吗?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东西呢——如果减掉想象?不,还不是“想象”。并非实实在在有个现实,此外还可以有虚构的想象。我说的和Einbildungskraft有点相像,但和“想象”或imagination离得比较远,因为这里说的主要不是飞翔而是一种穿透。凭借这种穿透,我们就会突破封锁,进入公共的世界,建立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实在联系。有了这种穿透力,一个俯伏书案的学者可以和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一脉相通,一个决心自杀的人和一个酣饮狂歌的人心心相印。反过来,缺乏这种穿透力,即使你处在事变的中心,即使你漫游世界,你仍然被封锁在一个小小乾坤里。因此,这种穿透力同时也是一种联系的力量。失去了这种力量,现实就被拧成一个小小的乾坤,而人们大概把“现实”专用来指现实被拧死了的这种极限状况。显然,富有生命力的个人和时代会在这样的现实中局促不安。在一个上升的时代,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人生展现为一个广阔的舞台。这时,古往今来上下八方都勾连成了一个共同世界。没有了想象,没有了穿透,屈原和司马迁,峨嵋的云海和南海的旭日,原子的碰撞和星云的膨胀,就都要从我们的生活中隔离开来。谁愿意说:看,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5月15日 22:50 苏州陈宅

明·文伯仁《沧浪清夏》图
叔叔和小琳陪到苏州市中心区观前街走走,苏州的供应情况不错,书店的开架书尤方便读书人。钱胆比任何时候都壮,因为叔叔给了我160元。
午饭时把这两日的谈话扼要重复一遍,然后叔叔和小琳送我上211次。在苏州停了两天多,在主人看来短得不近人情。这次周游委实太过匆忙,来不及吃饭,来不及睡觉,来不及思考,来不及写诗,来不及交朋友。其结果当然是经常腹中空虚,困不可支。不过,报上说,多活动少休息可以益寿延年呢。
车已开出苏州了,我守车门坐着,该利用这段时间盘算一下回京后的事情了。两个多月,拖欠的债务太多了。首先要向父母大人汇报此行(几十年来谁都不曾一下见到这么多亲戚熟人);老朋友们总得好好喝一夜吧;睡一觉;得看看侄女、侄女的妈妈和侄女的妈妈的双亲;应当看望导师,以及同窗;得把德语课接过来;得开学法语,接上希腊课;此外,可别忘了还得把论文改好,准备答辩;一路上受了许多惠待,交了几个朋友,写封平安信是比起码还起码的;应当坐在窗前读两本书;应当把游记整理一下;最应当的是:把这次旅行中培养起来的行进不息的精神坚持下去,那就可以把上述各项一一完成了。
16日 14:16 211次苏沪线上

新雅粤菜馆内部
到上海后,寻至南昌路。大伯极为热情。立即去买了大冰糕来吃。一面同大伯聊天,一面读家信,读到父母的关切,嘉明的扬逸,阿晖的亲切。未久,小玲来,她刚到过北京,每句话里都有“阿明”[即嘉明]两字,一时我忘了她是表嫂,还以为是亲嫂子呢。
今天是星期日。五点钟就爬起来,由大伯领到新雅,找不到座位,又转到杏花楼,在二楼找了个包桌,一人一元,像像样样地用了一顿早餐(茶、鸡肉包、蛋糕、馄饨、烧麦)。这两家都是上海最有名气的广东馆子,货色也确实好,不过为此挤车、倒车、赶路、占座,弄掉两个钟头。
在深山密林里,当然是我自己拿主意;但城里所拜访的多为长辈,我只有听命而已。八点半到姑姑家,一见面就坚留午饭,大伯事先同我约定,坚不肯留。姑父从信中知我将到,特将白班调成中班,准备陪我几天,哪料我只坐片刻。如此面对长辈,多少有点左右为难。各地亲戚都当件正经事准备招待,我却到处行色匆匆,说是拜访尽人情,说不定反伤人感情呢。
大伯阻挠我在别人家用餐,是他自己定要请我,出姑姑家就绕回新雅。大伯很讲究吃食,点一小盘炒虾仁就三块五,让我这个“牛吃蟹”三口两口扫干净了。
到多伦路,黄家正要用午饭,听说我第二日就动身,黄伯伯颇感意外。他已经为我安排了好几个节目。我答应随他去拜访几位老长辈。黄伯伯饭也未得安吃,为我开了赴青岛的介绍信,然后就带着我不断坐车,换车,弄得我这个大笨蛋全不知南北,到了金先生家;不在,金伯母刚端上茶来,我们就告辞。去看伍医生,从午觉中唤起,闲谈了不久,又去看陶先生,也是从午睡中唤起的,虽已下午三点。先生很热情,这回坐得久些。他是老革命,后来“犯错误”(那口气是男女错误,或财务错误),降为现在这个校长。接着去访庞校长。庞校长已退休,正图恢复中职学校大业。早听说我要来,一直在等,这时却在南京庞公子处,说第二天就回来,却也不及见面。留一片纸,退下楼来。
亏得黄伯伯念我时促,决定不去拜访另几家更远的。这些老先生老夫人,都是和蔼可亲的,但毕竟陌生,所关心的事情不同,而寒暄又非不肖之所长,在这一连串“礼节性访问”中,坐立之间,手足无措口舌拙滞。一生过半之人,被领到东领到西,被例行夸奖一番,总有些不自在。
黄公陪着到霞飞路转服装店。看来买衬衫比写毕业论文难不少。黄公又不是喜欢替别人做主张的,始终笑立一旁。只好作罢。
到四川北路,黄伯伯把东宝兴路的三层旧宅指给我看,一面给我讲些往事。平时大都市里不觉日月之光,这时却眼见着斜阳醒目地照在楼壁上。
回到黄家,应请把我的旅行观感乱弹了一通。尊长面前原应藏拙,但已相处得随便,太拘谨倒见外了。黄师母教我一定要买衬衫,“不会买是一回事,不买又是一回事”。
辞还南昌路,大伯已睡。写几封信,包括给你的这最后一封。信到,我人也到了。最后再向父母转达一次问候吧,23日就当面请安啦。
17日 午夜 上海南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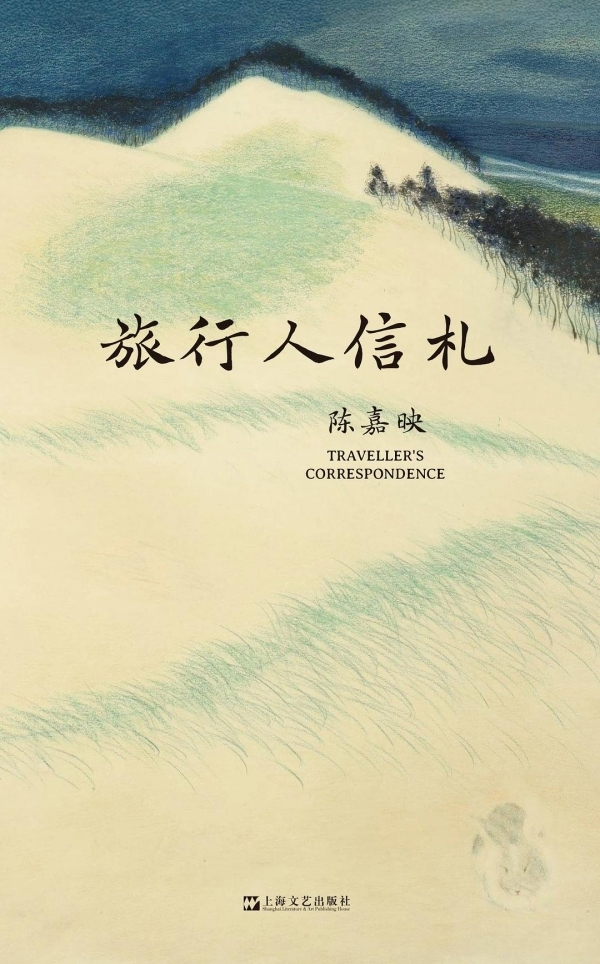
《旅行人信札》,陈嘉映/著,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eons,2025年2月版
上一篇:25岁属猴生肖。
下一篇:澳洲签证价值观声明,尊重与诚信









有话要说...